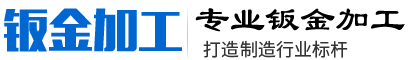1. 今天,红黄绿码这一系列可视化系统及其相关的治理和动员举措,在中国已经成为基础设施。
2. 凡是基础设施就有公共准入性,而且不可以任意指定或设置个别接口。如地铁、电力这样的基础设施,指定某些个体不准使用会造成什么影响?
本研究讨论中国的可视化作为基础设施,发表于专门讨论新媒体技术的国际期刊Convergence 2022年第1期。这里翻译部分相关段落,以供参考。
可视化系统作为基础设施: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数据可视化政治及其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数据可视化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的崛起。新冠疫情期间,我们选取了深圳为案例,展示作为数据中介的可视化系统对于政策和社会的影响。我们提出了一种将可视化系统看作基础设施的认识论:在中国,可视化已被发展为一个技术系统,用以支持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和集体行动。为此,提出了三个特征来描述中国新冠疫情期间的数据可视化政治,特别是总结了数据可视化中代理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此外,基于可视化、基础设施和数据政治概念之间的概念化,我们认为,可视化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容易被忽视的技术过程。数据的创造和使用似乎是不言自喻的行为,但可视化实际上支撑着背后对数据政治问题的感知、参与、提议、批判。通过与深圳公共卫生部门成员的焦点小组讨论和对深圳居民的深度访谈,我们搭建了一个定性的效果测量框架,强调了可视化参与政治和行动主义的潜力。
近几十年来,可用数据量出现了指数型增长,吸引着人们去收集、检索和分析这些数据 (Breiter and Hepp, 2018; Cukier and Mayer- Schoenberger, 2014)。然而,未经分析的原始数据集可能难以理解 (Gray et al., 2015)。正如Hilbert 和 López (2011) 指出,数据的生产和存储可能比数据的分析速度要快得多。因此,数据可视化作为一种高效的分析和展示手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数据可视化可以被定义为使用各种图形化手段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展示,帮助研究人员得出结果并促进读者理解(Foucault and Meirelles, 2015; Kennedy, 2015)。这些图形化手段包括柱状图、折线图、散点图、地图、可视化平台/系统等(Aparicio and Costa,2015)。数据可视化被用于学术研究,也被用于信息的公开传播(Bucchi and Saracino,2016;Kennedy and Allen,2016),例如在新闻机构、政府和NGO组织中。信息设计、数据新闻等专业实践也使得数据可视化越来越受欢迎(Knight,2015)。
数据可视化在政治和权力运作的现实世界中也发挥着作用(Nærland,2020)。例如,数据可视化的目的之一是检测趋势或异常值(Foucault and Meirelles,2015),从而帮助商业或政府决策(Ruppert et al.,2015)。一些研究指出了开放政府数据(OGD)的意义(Graves and Hendler,2013;Hilbert and López,2011),声称政府作为公共数据的提供者之一,也应该是数据可视化的生产者和倡导者,以支持基于证据的政府内部决策(Robinson,2016),以及面向受众的说服(Emerson,2008)。数据可视化在政治议题上的重要性显然已经引起了关注。我们最初的研究兴趣是,可视化是如何通过调解数据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并在政治议题上发挥作用。
Ruppert等人(2017)对 数据政治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前景的道路。他们将数据政治的概念定义为关于围绕数据收集及其应用的政治斗争,以及数据如何在不尽相同又相互联系的尺度上产生新型的权力关系和政治。他们提议将重点从数据化转向社会实践和代理人,并声称数据可以被视为结构化后的知识对象。不同领域的代理人以及他们的利益催生了专业知识、概念和方法,供他们在权力和知识的语境下使用。这篇文章研究了社会数据化的一个新兴范畴,即数据可视化。我们认为,数据可视化调解了数据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采用视觉来重新编码数据的权力和知识领域,并可能参与[重新配置]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Ruppert et al.,2017)。
因此,这份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期间的数据可视化系统,以揭示数据可视化政治的出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疫情提高了人们对信息及其可视化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允许收集和分析流行病学数据 (Xu et al., 2020)。基于新冠疫情的数据可视化也会以各种形式呈现,用来描述一个政治/地理区域的整体情况,产生公共卫生建议和政策。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以深圳为例,介绍了深圳的数据可视化实践。深圳拥有1756万人口,截至2021年8月31日,累计有431个本地确诊病例和143个境外输入病例。深圳公共卫生部门因其出色的表现和持续创建新冠疫情数据可视化而得到其他城市的认可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2020; Zou et al., 2020)。在本文中,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首先,数据可视化与政府组织的运作和政策决定有关。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数据可视化可能是广泛的资源、权力分配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提出了以下两个主要的研究问题:以新冠疫情为例,数据可视化在中国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从政治和行动主义的角度来看,数据可视化有效性的新定义包括什么?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一,我们梳理了相关文献,回顾了关于数据可视化的政治意义和有效性的讨论,以确定本研究的理论位置。第二,本文介绍了在新冠疫情期间数据可视化如何动员集体的案例。第三,我们提出了对作为中国社会基础设施的可视化实践的见解,分析了中国数据可视化政治的特点,然后跳出新冠疫情的案例,将 作为基础设施的可视化 概念化。接着,我们强调所提出的分析结构对数据政治的理论意义 (Ruppert et al., 2017)。通过与三位代理人(分别是部门主任/经理、设计师、编辑)进行焦点小组讨论(FGD),以及与17位深圳居民进行深度访谈(IDI),我们讨论了数据可视化的参与因素与有效性定义,并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定性框架,来帮助进一步理解,可视化如何作为在公共紧急情况下成为支持政治参与和行动主义的工具箱。
可视化是一种交流数据的方式。大量文献指出可视化在改善认知和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 (e.g. Tufte and Graves-Morris, 1983; Card, 1999: xiii)。一些研究探究了数据可视化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一般来说,数据可视化和政策决定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数据可视化本身是一种公共政策行为。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承诺在OGD框架内分享数据(Dawes and Helbig,2010),而数据的可用性是可视化的前提条件。第二,数据可视化为决策前的知识发现提供了证据。从Snow(1854)的Broad Street Pump Map和Nightingale(1858)的Rose Map开始,数据可视化被认为具有知识发现的潜力(Grinstein and Wierse,2002;Drucker,2010),并减少决策者对最佳决策的不确定性(Robinson,2016)。尽管政策制定通常被认为是非线性的(Shaxson,2005),即基于更广泛的信息集合,但人们承认,数据可视化为政策形成或改革提供了支持,至少对政策倡导者(NGO、记者、研究人员等)来说是如此,并且可以提供 可能的解决方案来弥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差距(Ruppert et al.,2015)。第三,数据可视化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政策说服和动员。政策倡导者传递知识和证据,帮助政策制定者(Williamson,2016)传播新的理念和规范,并进行社会部署。在这个过程中,数据可视化的公认功能随之体现出来,例如,降低理解难度(Kellehe and Wagener,2011),加快理解速度、节省时间(Chen et al., 2014),提高信息的准确性(Otten et al.,2015),以及为感兴趣的人提供开放式的发现和探索手段(Foucault and Meirelles,2015)。数据可视化有可能部署有效的沟通和有说服力的宣传活动,以促进政策实施(Hagen et al.,2019)。从前面的相关研究回顾来看,数据可视化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链可以确定为:知识发现→政策制定→政策说服与动员。这个链条涉及三个群体,即政策倡导者(研究人员、专家、NGO、记者等)、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和公众(居民等)。
对于一个希望其居民迅速了解情况并遵守政策的政体来说,文字描述和数据集可能不是最有效的展示方法。因此,2020年2月起,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发达城市率先采用了流行病学数据可视化的做法。除地方政府外,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公共卫生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过展示全国趋势和各省状况领导了可视化工作。此外,通过使用政府收集和共享的数据,学者、NGO、新闻机构和公民数据科学家被鼓励加入可视化工作——作为数据的代理人和倡导者,提高社会对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认识。他们不断地分析流行病学数据,并创造各种可视化作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证据甚至是解决方案。因此,不同的可视化作品可能源于不同的生产者,形成了一个数据及其代理人的混合系统。在图1展示的六种主要的可视化方式中,(A)和(B)的生产许可证是由政府颁发的,因为数据是与个人身份证相联系的;并且(A)和(B)的输出是智能手机,只有特定的个人身份证持有人可以访问,以保护隐私。相比之下,(C)至(F)可能来自政府或其他主体,与电视、报纸或数字媒体渠道兼容。特别是,位置地图(F)是平台企业、公民数据科学家和政府部门合作的结果,经常作为一项功能接口被嵌入到其他中国大型应用(如微信、支付宝)中。
2020年2月,在中国开始抗击新冠的一个多月后,不同的可视化作品得到了互联互通的机会。一个可视化系统以四个阶段的模式呈现,覆盖了从街道到整个国家的地理区域,从而在引导和与民众对话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图2)。
基于对中国抗疫早期(2020年1月至6月)的回顾,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视化系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虽然电缆和硬件、卫星、微芯片、数据中心设施和半导体等元素构成了互联网本身的信息基础设施,但这同时鼓励了其他基础设施的分裂(Plantin et al.,2018;Van Dijck,2021)。我们从专注于基础设施研究的学者那里得到启发(Edwards et al.,2007;Star,1999;Star and Bowker,2006),并建议考虑Star(1999)的建议,从关系和生态的角度看待基础设施,而不只是作为事物。在这个案例研究中,对作为基础设施的可视化系统的讨论是我们对可视化、基础设施和数据政治之间的联系进行进一步概念化的先决条件。
首先,流行病的数据可视化是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的,它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新冠疫情)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抗衡。中国的数据可视化工作采取了混合机构的模式,政府负责可视化的开发和运营,提供明确的标准和社会承诺,同时也鼓励其他行为主体分析和展示数据。第二,数据可视化是无处不在的。数据可视化已经嵌入到中国人高度的数字化生活中,成为新冠疫情期间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元素。截至2021年1月,在微信和支付宝等超大型数字平台上,可视化积累了9亿中国用户的400亿页面浏览量(CNNIC, 2021)。
在抗疫过程中,数据可视化提供了对无形后台内容和数据流的强制持续访问。更重要的是,数据可视化被嵌入到现有的通信网络和物理基础设施中,作为支持访问开放协议的数据可视化技术 (State Market Regulatory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2020),这是网关的典型案例(Klose,2015)。网关是基础设施中社会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提供了允许新系统访问框架的接口(Edwards et al.,2007)。例如,健康码的可视化操作是基于虚拟和物理设施,如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整合到与物理表面(如公共场所的柜台和提示板)联网的二维码,以及实时上传和分析个人数据的算法设备,从而反映整个城市空间的人与机器的混合系统。最后,还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对数据可视化的依赖。对于政府来说,返回的可视化结果被用于政策决策和宣传。对于公众来说,数据可视化类似于交通信号和地铁地图。公众必须学习和理解可视化,以更新他们对城市空间的警惕程度,以及提醒自己要做什么、不要去哪些地方的认知地图,从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技术再物质化。如果可视化系统或相关算法消失、崩溃,可能会引起社会混乱。
基于所展示的指标,我们提出数据可视化系统在面对公共紧急事件时成为当今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论证这种关系里包含了重要的行动者群体,特别是这个行动者群体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
因为可视化提供了一种使公众更接近数据结论的概念和生态,这也就意味着它可能支持新兴数据政治问题的运作。在Ruppert等人(2017,2020)对数据政治和数据公众,包括数据代理和行动主义的讨论中,我们意识到,可视化是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技术过程。这种基础设施的可用性是被假定的:这种基础设施对于支持“前台”主体对数据的感知、参与、提议和批判是必要的,并通过数据分析和数据新闻等专业实践来协调竞争和权力配置,这一切很难通过未经可视化解释和连结的原始数据实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实践中,可视化已经成为人们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交通信号灯一样普遍。我们当然关注到,可视化被赋予了操作权力的特质,并进一步隐藏了数据后台的透明度,从而减少了对数据来源和处理细节的披露,难以在不同行为者的代理中揭示事物的本质。从实践到概念,我们展示了可视化如何作为基础设施发挥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可视化政治,以扩大对数据政治的讨论。
原标题:《可视化系统作为基础设施: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数据可视化政治及其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